从1984年大学毕业进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工作开始,35年田野考古,郑同修主持了数十项重要的考古发掘,并以其在秦汉考古、周代考古和大遗址保护等领域的丰硕学术研究成果,成为国内考古界的大家。2019年8月31日,郑同修正式到山东博物馆报到,履新山东博物馆馆长一职。从考古大咖到省博掌舵人,华丽转身的背后,是郑同修对考古、文物、历史刻入生命的热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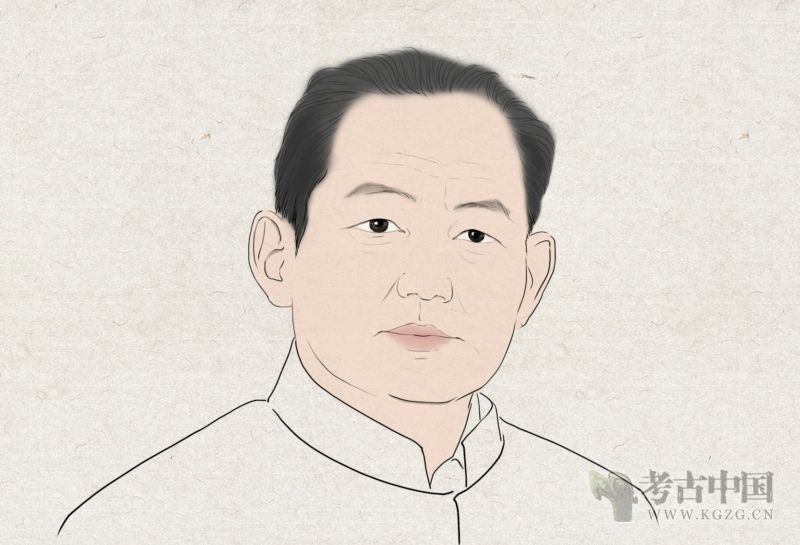
▲ 图片由孙婷婷 绘
一旦深入进去,考古魅力无穷
或许是因为长年野外考古的原因,郑同修身上带着考古人独有的质朴、硬朗,说话大声,直奔主题,永远平易近人。如今早已是国内考古界大家的他,最初与考古结缘,完全是误打误撞。1980年郑同修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先上了一个学期的公共课,然后开始分专业,“考古专业要在我们123个历史系学生中招20个,倾向于农村学生和对古文献比较熟悉的学生”。郑同修虽然来自农村,但觉得想进20个名额不太容易,何况自己对考古一无所知,所以就没有报名,“后来是我同宿舍的同学去报名,出门时跟我说要不也给你报上吧,结果我学了考古,他反而没学”。
1984年大学毕业,郑同修进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一干就是35年,“从没挪过窝,因为考古是一辈子的事情”。他觉得,一旦深入进去,考古魅力无穷,“这是一门不断发现的学问,每天,每个小时你都会有新的发现、会产生不同的认识。比如你发掘时发现了一个杯子的口沿,心里就会想:它是完整的还是残破的?随着清理工作的推进,杯子的形态也渐渐露了出来,一系列的问题又浮现了出来:它是什么年代的?为什么会放在这里?它和周边器物的组合又意味着什么?等等等等,每一件文物的发掘过程,都会产生不同的认识,趣味无穷”。
因此郑同修觉得,一个真正的考古人,一定愿意把考古当作自己终身的事业。不过在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上对考古却不是这么认为的,因为考古工作需要长时间在野外,当时流传着“有女不嫁考古郎,一年半载守空房”这样的俗语。这俗语不是空穴来风,那时的考古工作异常艰苦,长时间在野外不说,“常常需要徒步翻山越岭”,“那时候,有辆自行车就不错了,我曾经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邹平到临淄,140里路,骑了整整一个上午”。夏受炎热,冬忍寒冷,冷暖自知,郑同修至今记得那时候做考古调查时住在乡村小旅馆的情形,“地上全是鸡屎鸭屎鸡毛鸭毛,晚上睡觉,为了不弄脏内衣裤,要么穿着外套睡,要么脱得一丝不挂。白天搞调查,晚上在小煤油灯下写调查报告,苦不堪言又乐在其中。现在想想,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
真正让郑同修“痛苦”的,是“挖哪儿哪儿空”的烦恼。从22岁开始,郑同修就基本上能独立在考古工地工作了,1988年参加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1989年取得考古领队资格,此后几乎整个上世纪90年代,郑同修主持的考古发掘,几乎都是“挖哪儿哪儿空”。“比如寿光三元孙,158座古墓,只出了不到50个破陶罐、6枚铜钱”,这让郑同修心生惶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究竟适不适合干考古。他向大学时的老师栾丰实先生倾诉,栾老师鼓励他坚持下去,“山东没大有搞汉代考古的,坚持下去定有所成”。考古专家完胜盗墓分子
郑同修坚持下来了,于是,神奇的事情也发生了:由他主持的考古发掘项目,从“挖哪儿哪儿空”,变成了“挖哪儿哪儿有”“挖哪儿哪儿都特别重要”。
“转折点”是在2001年,这一年,郑同修主持发掘了费县西毕城墓地,“当年就发掘古墓葬1660余座,而且全部保存完好。之后又陆续进行发掘,总共发掘了2000余座墓葬,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仅陶器就有约4000件,铜镜230余面,玉器100余件,另有大量的钱币、铁器等。”迄今为止,西毕城墓地依然是山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
自费县西毕城墓地发掘后至2004年,郑同修先后主持发掘了日照海曲汉代墓地、临沂洗砚池晋墓、青州西辛大型战国墓,这些发掘项目连续4年入选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其中,日照海曲汉代墓地、临沂洗砚池晋墓分别获得2002年、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8年,由他主持发掘的高青陈庄西周城址发掘项目,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30多年考古发掘,令郑同修难忘的经历数不胜数。比如那次青州西辛战国墓的发掘,堪称“考古专家完胜盗墓分子”的传奇。西辛战国墓非常大,南北长达100米,椁室就有9米见方,全部用数吨重的大石块砌筑而成,石缝中又以熔化的铁汁浇灌。但这个墓被盗得非常严重,“发掘前我们发现的盗洞多达26个。椁室里早已被盗一空”。那一年,郑同修正好随国家文物局去欧洲考察,走之前他交代考古队员不要着急,等他回来再进行墓室发掘,“结果他们的工作比较快,等我回来他们就已经把工作做完了,准备撤工地了。我到了现场,越看越觉得不对。古代的大型墓葬,若是被盗,金银器和青铜器会被盗走,但盗墓人一般不要陶器,甚至会把陶器砸碎,而且即便被盗走了,青铜器也会遗留下铜锈等痕迹,但我却没发现任何铜锈和陶器碎片。我就说,‘先不要撤工地,继续发掘。我们把整个石椁拆掉,一直往下面的青膏泥挖’。果然就在贴着大石椁的最底部发现了一个木盒子。木盒子虽然已经腐烂了,但是里面装着的青铜器、玉器、金器、银器都还在,我说行了,这下可以撤了,该有的都有了”。
日照海曲汉墓的发掘也让郑同修毕生难忘。为了保护古墓中的珍贵丝织品和漆器,郑同修决定把一直泡在水里毫发无损的木棺整体搬入日照市博物馆再进行仔细清理。那是五月底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一切准备就绪,狂风大雨却反复降临,从早晨6点多到晚上8点多,14个小时,郑同修没来得及喝一口水,吃一口饭。包括“北方最美的500件漆器”在内,海曲汉墓发掘成果极为丰硕。对郑同修来说,14个小时不吃不喝,“不是事儿”。
35年田野考古,郑同修的科研成果亦是硕果累累,其代表作《山东汉代墓葬出土陶器的初步研究》通过研究出土陶器对山东汉代考古进行了科学分期,一举奠定其山东汉代考古权威的学术地位。多年来,他还主持或承担了多项国家大型课题研究项目和中外合作研究项目,编辑出版《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出土镜范的考古学研究》《山东重大考古新发现》《辉煌三十年》《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山东卷》《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山东卷》《临沂洗砚池晋墓》等系列考古报告或专著,发表一大批研究论文和考古报告。
因为一座博物馆,爱上一座城
郑同修曾笑言自己的简历“极其简单”,“一条山东大学毕业,一条在省考古所工作,没了”。但2019年8月31日,他的身份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变为山东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和博物馆学有相通之处——都是与文物打交道,但两者又有着本质的不同:考古的基本职能是发掘、研究文物,博物馆的基本职能是宣传和教育。在郑同修眼里,考古更为单纯,博物馆作为面向社会的窗口,则涉及面更广,“通过一座博物馆,爱上一座城,爱上山东大地。这是我们博物馆人应该努力的方向”。
基于对博物馆基本职能的认知,郑同修认为,博物馆的发展必须要有开阔的思路,“首先必须加强科研,培养科研梯队”,在他看来,博物馆的宣传、教育职能,需要通过文物的收藏和展览来实现,而学术研究又是办好展览的前提,“展览不是摆上文物就行,而是要研究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文物本身不会说话,得有专家通过深入的研究来让文物说话,让文物活起来”。
在郑同修看来,盘活文物资源同样重要。他对山东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构想,拟举行一次全省的博物馆馆长座谈会,成立山东省博物馆联盟,“摸清馆藏文物,盘活全省文物资源,策划重量级展览并在全省乃至全国巡展,如此才能让文物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
建设“智慧博物馆”是郑同修的另一个重要思路。在4月13日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郑同修介绍,山东博物馆积极打造数字展厅,实现了13个实体展览的数字化展示,让观众能够足不出户,云游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推出12期“海岱微讲堂”,为观众讲述“齐鲁瑰宝的那些事儿”。“文博公开课”将文物修复室搬到了互联网上,阅读量达135万。推出了5期“云博物馆”系列直播看展活动,单场全平台观看量突破1000万人次。此外,山东博物馆前不久还联合湖北省博物馆共同举办了“5G重构想象跨时空协作活动”,这是在全国博物馆中首次探索利用5G技术,将教育活动向社会公众展示的新突破。郑同修认为,借助科技的力量打开博物馆的边界和场景,是博物馆必然面对的挑战和机遇。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